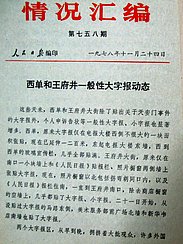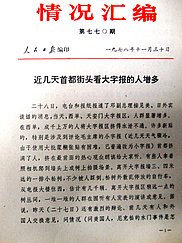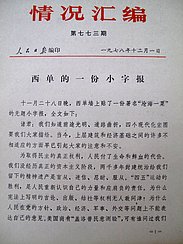内部报道给领导人介绍民主运动
我觉得是这杨:民主墙分三派,第一派,主要力量是徐文立、刘青和杨靖三个人为代表的《四五论坛》。徐文立 …… 年龄和瓦文萨一样,文化大革命也受了挫折,不是特别大。他们基本的口号就是小民议大政,反映了市民阶层,底层的工人阶级,或者叫弱势群体的一种议政参政的要求。第二派是左派,民主墙的左派是《北京之春》,团中央委员周为民是总编辑,团中央候补委员王军涛是副总编辑,还有吕嘉民,十一个编委中大概有九个高干子弟,主要是四五英雄。他们对三中全会、中央工作会议知道一点消息,实际上是站在党的范围里最激进的路线。第三派,也就是右边的,是魏京生,魏京生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,他的《探索》提出“五个现代化”。四个现代化,政治部现代化,他不干。他对个人崇拜有看法,担心形成对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,汪东兴、华国锋就更不在话下。(唐欣,9页)
虽然这是内部报导,但显然与警察、安全部门上交的报告性质不同。那些部门是按敌情动态上报我们的,而这次的内参,语气虽然不是明显的褒扬,但看得出来,在力求客观公正。内参不是哪个记者可以随意写的,这必然来自一个指示,它对民主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与民主墙来往的人不乏手眼通天者,不久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份内参。记者在文章头一句就说,他来到联席会议,感觉象到了月球上,那里是另一个世界。 (刘青,唐欣与联席会议)
除了描述组织,对个人的介绍,是唐欣文章的重点。大约有十来个人在他的文章中都有一段单独文字。我记得《四五论坛》有我和徐文立,《北京之春》有韩振雄、王军涛和周维民,并且特意提出了年龄很小的林刚,《今天》谈到了北岛和芒克,还有魏京生、任畹町等一些人。文章中对《北京之春》的几个人,用的是褒扬语词,说他们都是四五事件中的天安门英雄,有好几个团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,来自中层以上干部家庭,政治嗅觉和素养较高,政治立场很鲜明,往往比中央的战略部署先走了几步。对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的成员,用词上就有所变幻,比如我们《四五论坛》,说我们大多是工人,主要热衷于搞组织和组织活动,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特点。唐欣的文章显然来自一种印象,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。《四五论坛》单是在总部的成员,就有好几个人很擅长于写,而在《四五论坛》的全国通讯成员中,更是集中了许多杰出的笔杆子,如王希哲、陈尔晋、孙丰和徐水良等人,民主墙优秀的作家理论家,有一半与《四五论坛》有关。不过唐欣说《四五论坛》大多是工人是对的。唐欣本人是高干子弟,他当然对背景相同的思想语言更容易理解。 看过这篇文章,有一些现象很耐人寻味。有些没有被视为思想反动或危险的人,脸上笑迷迷的,说这次老魏老任他们可不舒服了。不仅背后有人这么说,我记得魏京生任畹町路林等人来联席会议时,也有人高声大气的告诉他们,他们这次可出了名,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意识的名单,是交给中央政治局看的内部参考上。魏京生任畹町他们则显然心情沉闷,没有从这份参考中感受到可笑和有趣。他们大多都讲了如下意思的话:它一份内部参考说了就算定案吗?说由它说,干归我干,不会为这么两句话哆嗦打颤,今后只会干得更欢。我的感觉是,这次内参上的报导,对有些人有不小的刺激,很可能往前冲得更猛更远。其实,联席会议那时应该作出分析和判断,以便利用有利的方面,对不利的部分进行些必要的修正,才会有利民主墙的发展。因为内参上的报导,只是官方一个模糊的意识,并不是一个要镇压的信号,那时候官方更愿意做的,可能是对民主墙加以指导甚至招安。(刘青)
唐欣是直接敲敲门,推门而进的。当时,我正与《北京之春》的林刚在聊天。林刚只有十九岁,象《北京之春》的其他成员一样,有两个特征:出身高干家庭,因为七六年的“四五运动”曾经被关入监狱。他说他是代表《北京之春》与联席会议联系的,恰好也是第一次来,在唐欣之前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。唐欣对我们看看,说哪位是联席会议的刘青,他介绍自己是《北京日报》的记者。他甚至掏出了记者证给我看,笑眯眯的直看着我们,那态度不象在炫耀,而是在突出他的坦诚和取信于我们的意愿。他找我是属于工作,这与那些虽有官员的身份,但是私人询访的情况大不一样。 唐欣说,民主墙成了世界注目的新闻,中国新闻界反象睁眼瞎似的对此不闻不问,这情况有点象笑话。他是希望不要把新闻都便宜了外国人,此来只是想了解点情况,没有任何其他意思,请不要多想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,这反倒象在引导我想。不过不论我怎么想,都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。面对不时听说到特务奸细的传闻,我们内部早有谈论,要坚持公开坦诚,就是警察来访,也同样欢迎。我把这话告诉了唐欣。他那白净的脸扭向了我,说“是吗?”但是看上去他并不感到惊讶。唐欣的兴趣很广泛,他与我谈论民主墙、当前的社会思潮、各民刊的特点以及各民刊的主要成员是哪些。不过,我还是感觉到他有着轻重的区别,他的真正兴趣在各民刊的情况和那些主要成员上。我想,如果是这样,我倒可以做些安排,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公开坦诚。于是我告诉他,那天晚上恰好要召开联席会议,他如果有兴趣,可以来列席旁听。这次他挑起了两道眉毛,说“真的吗?”(刘青)
这天晚上来的代表比较多,有些民刊来了两个代表,如《探索》就来了路林和魏京生,《四五论坛》除了我,还来了杨靖,有一些人则是不邀自来。我曾告诉林刚,也邀请《北京之春》派个代表来列席,不过来的还是林刚。代表到的比往常开会时间早,我请人通知的时候,告诉代表们,在与第一个公开的官方人物接触前,我希望有时间先向大家介绍一点情况。翻一翻共产党的历史,新华社的记者在特殊情况下,常常起着微妙的作用。这毕竟是第一次接触,我们应有所协商准备。大家对官方主动找来,兴趣大于警惕,我记得我们似乎就没有警惕。我们捉摸的是:唐欣会不会如他自己所言,要对民主墙及联席会议采访,要在报纸上发表客观介绍的文章,还有指挥他来的是什么派系的政治力量。我们有些兴奋,甚至是得意和高兴,我们这些民刊和民众组织终于得到某种形式的重视,也可能蕴涵着强大的发展机会。有人说,想一想,如果报纸上发表介绍我们的文章会怎么样?唐欣比约定的时间晚来了一个多小时,他说是为了让大家在他来之前充分讨论,以便确定是否同意他列席联席会议,他还玩笑似的加了一句,时间宽裕些还可以商量对待他的态度和愿意谈的内容。看来,他比我们想得又多又怪,他这么想怕是有他的原因和道理。他脱下大衣,又立刻掏出了记者证,逐一递给每个代表看。这使大家有些觉得突然,记者证仅在大多数人手里沾了一沾,有人甚至说,“我们还信不过你吗?”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不好意思胜过了好奇,当有人要把记者证还给唐欣时,坐在床上最边沿的魏京生与路林说了几句,路林便伸手接了过来。他们绝不是在手里沾一沾,但是记者证的封面和背面,他们就翻来翻去端详了一番。他们还真给唐欣提了两个问题,当然是面带笑容和讨教的口气,大意记得是问唐欣的记者证是不是刚发不久,以及是不是内参部记者。我有些不自在起来。不过唐欣还好,正在与其他组织的代表随意谈笑,似乎没有注意这边厢对他记者证的专注兴趣,对于讨教式的询问,他并没有停下谈话,只是自然的不加思索的回答几句。没有出现尴尬,我觉得这是一切会顺利的好兆头。 实际上,唐欣并不象他外表那样,对魏京生路林查看他的记者证毫不在意。在他写给中央看的内参里,有一整段文字描述了这一过程。虽然唐欣对此的结论是,《探索》的成员心细,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对他比较容易相信。但是这话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——《探索》成员对政府来人怀有深深的戒意,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对政府没有太大的戒意,而有没有戒意,是与政府的感情的标帜。这自然不是对《探索》的正式定位,唐欣在他所写的内参中,对《探索》还有正式的记述,是将其归入了激烈和有问题的一类。大致上,唐欣将民刊和民众组织也分为三类,而且各组织在哪类,与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差别不大。区别在对各类的看法上,我们说第一类是激烈派,唐欣不仅认为激烈,而且定位在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意识形态,认为有危险倾向。划入这一类的,还有“中国人权同盟”等。唐欣最看好的民刊,是《北京之春》和《沃土》,他对这两家几乎用的是正面肯定的词语。对《今天》,唐欣的文章也有所褒扬,说《今天》的在文学艺术上很有特点和修养。其他的民刊和民众组织,被划入了面目不清的灰色地带。(刘青)
我第一次去民主墙的时候是很担心的。民主墙当时有个《四五论坛》,是大刊物,写了一个联络地点,东四十条,是刘青的一个地址。去刘青那里前,还把我去哪儿写了一个小条,交给我的小妹妹。我说,万一我回不来了,你赶紧跟林伯伯 [林乎加] 打个电话,好来救我。去了以后,刘青挺热情的。我就开始接触民主墙,前前后后接触了几个月,认识了一百二十五个人物,包括顾乡(顾城的姐姐)、吕朴、吕嘉民(即《狼图腾》的作者姜戎)、周为民、王军涛、徐文立、魏京生、赵振开(北岛)、姜世伟(芒克)、《沃土》的胡平, 还有姜洪这些人。 。(唐欣,8-9页)
除了描述组织,对个人的介绍,是唐欣文章的重点。大约有十来个人在他的文章中都有一段单独文字。我记得《四五论坛》有我和徐文立,《北京之春》有韩振雄、王军涛和周维民,并且特意提出了年龄很小的林刚,《今天》谈到了北岛和芒克,还有魏京生、任畹町等一些人。文章中对《北京之春》的几个人,用的是褒扬语词,说他们都是四五事件中的天安门英雄,有好几个团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,来自中层以上干部家庭,政治嗅觉和素养较高,政治立场很鲜明,往往比中央的战略部署先走了几步。对其他民刊和民众组织的成员,用词上就有所变幻,比如我们《四五论坛》,说我们大多是工人,主要热衷于搞组织和组织活动,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特点。唐欣的文章显然来自一种印象,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。《四五论坛》单是在总部的成员,就有好几个人很擅长于写,而在《四五论坛》的全国通讯成员中,更是集中了许多杰出的笔杆子,如王希哲、陈尔晋、孙丰和徐水良等人,民主墙优秀的作家理论家,有一半与《四五论坛》有关。不过唐欣说《四五论坛》大多是工人是对的。唐欣本人是高干子弟,他当然对背景相同的思想语言更容易理解。 看过这篇文章,有一些现象很耐人寻味。有些没有被视为思想反动或危险的人,脸上笑迷迷的,说这次老魏老任他们可不舒服了。不仅背后有人这么说,我记得魏京生任畹町路林等人来联席会议时,也有人高声大气的告诉他们,他们这次可出了名,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意识的名单,是交给中央政治局看的内部参考上。魏京生任畹町他们则显然心情沉闷,没有从这份参考中感受到可笑和有趣。...... 我的感觉是,这次内参上的报导,对有些人有不小的刺激,很可能往前冲得更猛更远。...... 内参上的报导,只是官方一个模糊的意识,并不是一个要镇压的信号,那时候官方更愿意做的,可能是对民主墙加以指导甚至招安。(刘青)
唐欣做为民主组织和党领导人的中间人
3月份逮捕了魏京生,4月5日逮捕了任畹町,因为“人权宣言”。这就有点不像话了。他们来声援魏京生,我那天在现场,便衣警察穿着球鞋,上头穿着便服,到那就起哄,然后还把民主墙的人往外国女记者身上推。我离开民主墙后哪儿也没去,直接就到了林乎加办公室。我如此这般一说----“你大白天的让这些人去起哄,给世界人都在看我们,这不是往我们自己脸上抹灰吗?”林乎加气得直拍桌子,然后就把公安局臭骂一顿,这也是公安局整我的原因。(唐欣,12-13页)
这个时候中央就变调了,说民主墙不搞了,四大自由都没有了。民主墙进了月坛以后已经稀稀拉拉,直到10月份又掀起一陈高潮。当时公安局已经整了我一份材料,这么厚,一卷宗。民主墙各个机构里头,几乎都有公安人员,他们文化水平可能也不高,整了这么厚的一个卷宗头目叫做《北京日报内参记者唐欣在民主墙非法活动》,就送上去了。送北京公安局党委,然后送市委,正好送林乎加桌上。林乎加一气,把这个一拍,然后就把公安局长叫去,说他们大水淹了龙王庙,他是我派去的。(唐欣,12页)
我到他家,他跟我谈了两个钟头。他还说,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,但是搁到大街上,西单这个地方稍微乱了一点,容易影响交通。他说,你回去跟北京市委汇报,跟林乎加同志谈一谈,能不能把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成为民主公园,就是中国的海德公园。 …… 第二天打电话就约见林乎加。林说,劳动人民文化宫就在天安门的旁边,那是不是也太显眼了,要是人多了,不是一样影响交通?建议把它弄到月坛。所以有一度,民主墙就移到月坛。这是我和《四五论坛》的刘青他们谈的,跟他提的建议。刘青一直没弄清楚我的身份是什么。 (唐欣,11页)
唐欣照例在提出他这一新想法之前要解释一番。这次,他不但郑重的反复的解释纯粹是他个人的主意,并不代表谁或是受谁委托而来,而且大谈特谈迁移民主墙的好处和必要。这次谈话时间也比较长,归结起来,唐欣大致强调了以下几点:民主墙不是一种长期的形式,民主墙地处交通要道,人员杂乱,上访的和瞧热闹的占了多数,长期下去,即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,也有碍观瞻、影响市容和国家形象,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的;民主墙最早曾经叫过海德公园,也确实想成为海德公园那样评议政治时事,发表自由言论的场所,就应该象海德公园那样,找一处清静的可以自由交流和演讲的场所,这样的场所最好也是个公园。最后,唐欣说他认为合适的场所是月坛公园,......
我同意唐欣的话有一定道理,...... 但是,唐欣这些话后面也隐含着明显的意图,我对这些意图感到不安。我说北京的民主墙是全国性的,它的存在与交通便利和人员繁多有极大关系,迁移到一个背静的地点,不仅外地人难以前往,就是北京人也没有时间精力前去,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民主墙。...... 我同时还提出一个稍微改动些的建议,就是将民主墙迁到天安门东侧的文化宫,或是西侧的中山公园,而且将迁往的地点改成免费公园,就可以免除唐欣所说的不足,又可以不影响民主墙的存活。......
后来提出了一个问题,就是民主墙绝对不能离开西单,离开西单就会落进圈套,自寻死路。这一观点的理由是,民主墙迁走就会与过去的历史和基本群众切割开,不会再叫做民主墙了,大量冲着民主墙来的人,包括国外的外地的,甚至北京的人,都会不知道去哪里找我们,我们又要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...... 唐欣对此沉默不语,好象已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大约八九个月以后,就在我被北京公安局无理扣压之后不多几天,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,取消“四大自由”,将民主墙的问题交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处理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即决定,取消西单民主墙,将民主墙迁往月坛公园。唐欣年初的所谓的纯粹个人主意,年底由中央指使北京市强力执行了。不同的是,民主墙这时已经失去讨价还价的有利态势。...... (刘青)
当时我主张中央和他们对话,就推荐王军涛和吕朴到乔木同志家里去。乔木同志当即就接见了他们。王军涛、吕朴跟乔木同志谈了很好,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。吕朴还想去找耀邦对话,对没对成我就不知道了。中央故意对话解决问题,也希望利用群众这种民主的热情为党的路线服务。但是觉得魏京生走偏了,你现在就开始清算邓小平的威信,这个路我们就没法走了。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看。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魏京生,恐怕他们是先进分子。但是当时没有“四项基本原子”,就没有改革开放。(唐欣,13页)
对联席会议表达出明显的招安或指导意思的,还是唐欣。虽然另外也有人表示与官方有联系,甚至表示我们如果愿意做某些变化,可以为联席会议与邓小平之间搭上桥,但是公开自己的官方身份,并且明说自己找联席会议属于工作性质的,这样的国家干部并不太多,唐欣是其中的一个。有趣的是,唐欣表达这种意思时,不管我会怎么想,却总是做许多相反的说明。唐欣往往在进行了一些漫无目的采访后,有个引人注意的停顿,声音也变得郑重起来了,他说,“我有一个想法,仅仅是我自己的,请注意,这想法绝不是来自任何首长或是机构,是我自己与你们多次接触后,不知怎么冒出来的主意,也许显得挺可笑的,但我还是要问问你。”如此的反复讲述中,他始终很注意观察我。我当然很好奇,也知道他要说的是重要事情,不过他那么不厌其烦的反复说明,倒叫我闹不清他真实的意思,是要我重视他所说的话,还是要我相信他所说的话。我笑着点头告诉他,我也常会产生些奇特可笑的想法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,我不会将那些想法讲给别人听的。唐欣终于说,如果让我还有民主墙的其他一些人,那些在青年中有些影响和威信的人,到团中央专职做青年的工作,一方面保持我们关心国事和敢说敢闯的特征,一方面有所组织和辅导协调,就是说由团中央给我们提供一块发挥作用的场所,我们对此会怎么想。(刘青)
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会面
我和胡乔木也谈过一次。他胡乔木就很坏。我在他家跟他谈的时候,我说应该解决腐败问题。他说:“腐败在哪个朝代都有,解决不了的,也没有必要解决。” 也有另外一些领导人,我们也谈过,都不如胡耀邦对我的印象深。后来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领导人,像刘延东,她是我的竞选顾问。我竞选的时候,她是我的顾问。她现在是政治局委员。
我很喜欢胡耀邦这个人,而且很敬重他。现在我也敬重他。从中国人的政治标准来看,他不太成熟,太容易被自己的敌人攻击了。而且我相信,邓小平想扶持他,想支持他,但是我也发现,他不大能够掌控,因为他太直率。...... 谈论了几个小时吧。本来他是想和我谈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。后来他谈得高兴了,我们就一起谈了几个小时。那天他说是牙疼在家,我觉得其实他是想和我们谈话,所以他留在了家里,没去上班。一开始我见到了秘书。我是以《北京之春》副主编的名义去的。后来他的秘书说:“你以这个名义不方便,这样吧,就以长辈见晚辈的方式来谈。”这样我就进去了。我和他谈了很多,总的来说我希望中国要进行改革,不要再搞政治迫害,不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中去。......
我明确说,我反对抓魏京生。胡耀邦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他拿出来一份简报,是贵州省委的,他说:“你看,贵州省委就抓了《启蒙社》的黄翔,后来又放了他,从生活上关心他。我主张这样处理问题。”他是反对政治迫害的。后来我说:“你应该搞政治改革。” 他说:“我想改革,想得牙都疼了,我睡不了觉,想中国应该怎么改革。不过,年轻人,改革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……
后来他还跟我讲:“年轻人你有三个优点,第一,你有理想;第二,你有知识;第三,你有干事的热情,有精力。但是你有两个缺点,第一,不现实,就是你没有从现实考虑做什么,光去想那些应该怎么样;第二太急躁,太着急。他说很多事情因为着急这样会把事干坏。” 所以那次和胡耀邦谈完,对我有很大的 … 为什么很长时间我并没有去想反对共产党,就是因为共产党内有胡耀邦这样一批改革者。(王军涛访谈录)
把民运积极分子邀请到共青团中央去”做青年工作“?
这确实出人意料。而且,这一趋向并不符合我参加民主墙的目标。…… 因此,对于唐欣的问题,我没有想一想就断然拒绝。我说,我参加民主墙可不是憋着受招安。唐欣听后颇有点尴尬难堪。…… 毕竟,提出这样的意向,说明官方还有多种打算,在中共高层的某些派系中,可能想对我们招安加以利用的意图,远比要镇压迫害的意愿大。……
唐欣并没有因为我的回答就止步,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,就是将他对我说的这些话,在联席会议上提出,听听其他组织的代表和活跃人士,对到团中央做青年工作有什么态度。我接受了他的要求,告诉他在最近的联席会议上我会提出。为这件事情,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。在特别会议之前,我已经与几个人提前交换了意见,如徐文立等人,他们同意和支持我对此所表示的立场和做法。开会时,我首先介绍了唐欣谈话的详细情况,分析了这些话的用意,以及可能来自什么地方,又讲述了我自己是怎样应对的。不过我着重讲的,是民主墙只有在独立时,才会是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力量,离开民主墙到官方机构去,不论事先答应给我们什么方便和条件,都不可能再有这种功能,实质也就变成人们常说的接受招安。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一些细节,许多人不厌其烦的要我反复讲唐欣说过的某几句话,如唐欣说没说什么样的人才算有影响和威信,显然有些人对这一提议挺有兴趣。不过,由于我在底下已经和一些朋友谈过,主持会议时又先表示了态度和观点,加上联席会议中没有一个代表愿意公开表示想接受招安,所以唐欣的提议并没有认真讨论。一番谈论之后,我们很快通过了两点决议:联席会议不接受到团中央做青年工作的设想;有组织或个人对此希望进一步了解,刘青可以帮助与唐欣接上关系。
一二天后,唐欣即来询问情况。看得出来,他对这样的结果有些不解和失望。我赶快告诉他,联席会议整体虽然没有做出接受他的想法的决定,但有些组织和个人可能有兴趣,他们希望对这个设想多一些了解,我请唐欣告诉我一个联系的方法,以便有兴趣的人可以单独和他联系。我想也许这点补充使他能好受些。我觉得唐欣对民主墙整体并没有敌视和恶感,尽管他将民主墙划分成好几派,并给一些派系涂上了危险的色彩。有一件事情,或许可以有助于了解唐欣对民主墙的态度。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唐若忻,是公开的与民主墙打交道很多的又一位官员,他和另外几位同事曾经以团中央的名义,写了一份关于民主墙的报告,详细介绍了几家民刊和民众组织及其代表,报告中有许多正面肯定和褒扬之词,还有一些对民主墙如何引导和发挥作用的建议。唐欣有一回就此对我说,唐若忻他们写的文章太多主观和感情色彩了,不如他的文章冷静和不偏不倚。因此,在中央上层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,唐若忻他们的文章产生的效果,是对民主墙的怀疑和猜忌,而他的文章才使民主墙得到了一定的了解和肯定。他当时对我分外亲近的说,想做好事也要知道怎么做才有效,急于往高里凑很容易,但不掉下来才叫本事。他用力握握我的手告别,显然他认为给民主墙动用过他的本事。他的话不足以令人信服,因为在对待民主墙的态度上,他的好感显然不如唐若忻那样坦诚明显。(刘青)